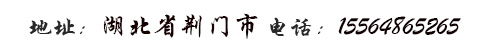叛逆的思想家1
| 叛逆的思想家ILGIRODELMONDOIN80PENSIERI作者:[意]皮耶尔乔治·奥迪弗雷迪(PiergiorgioOdifreddi)译者:姚轶苒约瑟夫·傅里叶认为,数学的主要目的是供公众运用和解释自然现象。但像他这样的思想家应该明白,科学唯一的终点是成为“人文精神之光”,从这点来看,数学问题与世界体系问题应具有同等价值。——卡尔·古斯塔夫·雅各布·雅可比《致阿德里安—马里·勒让德》年7月2日真正的哲学精神起源于18世纪中期,它并没有消除新、旧神学的争议,这些都不是它的探讨范围。我们随后将会谈论这些堪称“人类理性之耻”的问题。——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年写给你的前言常言道,脸是灵魂的镜子。如果真是这样,我的脸只能是一面空镜子了,因为我没有灵魂。当然,也许你希望或怀疑自己拥有灵魂,但实际上你也没有。相反,我们都有一张脸,却看起来很不一样。我能看到你的脸,却看不见我自己的。更准确地说,我可以从你的外部观察到你的脸,而我自己的脸却必须从我的内部去感知。对你来说,那是我的脸,对我来说却是眼角瞥见的一片阴影,将我与我的世界分离开来。或者说,将我的内在和外在形象区分开来。我可以用手触摸到这道边界,但它永远都是一道边界。我能看到你的脸,甚至能看到两张,每只眼睛一张。在我看来你是双重的,一幅上下颠倒的双重图像。因为我的眼球是两片透镜,它们将图像反转,把你的脸颠倒过来传输给我,下巴在上而额头在下,眼睛和嘴巴向反方向凸出。如果我对你闭上一只眼睛,就等同于把你的(或者说我的)缺点强加给我自己,我看到的你是有缺陷的:一个二维的女人。如果我闭上另一只眼睛,你依然是二维的,只有一点轻微的变化。如果我快速交替闭眼,当你惊奇地看着我,微笑着问我在做什么的时候,我只看到你在我的鼻子两侧跳来跳去。只有当我张开双眼看向你时,你的重影才消失了,我看到的是唯一的三维正像,而不是两个二维倒像。只有在我的脑袋里,你才不再是平面的,而终于有了体积,只有我的大脑具有立体感地超越了我的双眼所见。对我的任何一只眼睛来说,你不仅是平面的、上下颠倒的,还是模糊的。在中央凹里的你清晰而鲜艳,但那只是一个直径半毫米的区域。渐渐地,我将注意力集中到视线的最外侧,但不移动眼睛,你就开始变得模糊、黯淡了。同样,看到清晰鲜艳的你的还是我的大脑,而我的眼睛一直用一系列缓慢的颤动、迅速的跳动和高速震动轻抚着你的脸,好让脑的中央凹给你脸上的每一毫米定位,再合成图像。我再次看到你在我的视线里跳动,感知到你的无数图像碎片,就像是一幅立体主义绘画,只有我的大脑,能将它们合成一幅静态的古典画。数千张移动着的你的脸让我精神眩晕,却无法避免,想必到头来我还是有一个灵魂的:若真是如此,那么你就在那灵魂的最深处。但若我的大脑在眼睛不停地运动时没有抑制感知,那我可真得眩晕过去。所以,我的视觉感知是一个不断穿插着短暂失明的过程,唯有如此,你的脸方能从黑暗中浮现,在光线里显露。但没有一个瞬间我可以完整地看见它,因为一旦图像传递到了没有感受器的位置,视神经在那里远离了眼球,我就有了一个盲点。我的眼睛从未完整地接收到你,而我之所以没有感到有一个黑洞毁了你的脸,那只是因为大脑无数次帮助我,以在相邻区域感知到的信息为基础,自动将图像填补进去,把你的脸补充完整。我看到了一个彩色的你,但这些颜色并不是你拥有的,而是我给予你的。你脸上的光以一连串光子的形式出现在我的眼中。我的眼睛对它们不同的波长产生不同的反应,用虹膜的颜色为你着色,就像一个孩子用手指拿着蜡笔给一幅画添上色彩。我的蜡笔是视锥细胞和视杆细胞,视网膜承载着它们。当你的脸隐没在夜的阴影里时,我主要使用视杆细胞:在注视黑白色的你时,只有这一种类型的细胞可用。当日光重新闪耀起来,我便会使用视锥细胞,这种细胞有三个类型,为你填上绿、红、蓝三种色彩。但你并不像阿莱基诺小丑那样只显示三种颜色,这是因为我的大脑对它们的处理方式与声音不同,不是像音乐和弦那样完全区分开,而是在你的色谱里将它们混合起来。我没有把视锥细胞和视杆细胞理所应当地放在视网膜的前面,而是放在背面。这很奇怪,因为这样你脸上的光线就必须穿过整个系统才能到达我的成像感应器。但我就是这样被制造的,你也一样。章鱼不是这样,如果我跟它一样,就能像葛饰北斋画里的章鱼一样用触须包裹你。抱着这样的想法,我看到你是绛红色的,但我知道这只是大脑开的一个玩笑。那个颜色并不存在,而是你在同一时间产生的冷热反应所制造的通感,在你的脸上将红色和紫色美妙地混合在一起。你也许想要像我看你一样看到自己,我当然也想要像你看我一样看到自己。但我们彼此的愿望永远也得不到满足,因为我们都被限制在自己的头脑里,被迫只能看见别人而看不见自己。但在一幅画或一张照片里,我们可以部分感知到对方眼里的自己,尽管存在以下的限制:它们是二维、平面和静态的,而不是三维、有凹凸和动态的。另外,数字照片还会进一步引入一种间离元素,它将图像分解为一系列像素,就像一幅点画派作品。在电视或电脑图像中,这种间离能得到些许弥补,荧光粉和像素点用与视锥细胞同样的绿色、红色和蓝色为它们补色。屏幕上你的图像重新获得了在照片里失去的动态,因为即使我看不到你,你仍然会留在我的记忆中,这不仅仅是比喻,生理上亦是如此。如果你的图像以超过每秒50次的频率交替出现在我的视网膜上,它们瞬间的停留会让我无法意识到变化,我的大脑会把它阐释为因你虚拟的在场而形成的一种连贯的流动。在连续的图像中,若你的面部特征发生了轻微的偏移,大脑将把它们在连续的瞬间里空间上的接近理解为它们的移动。这种特殊的效果让你变得更加真实,尽管在试图拥抱你时,难掩我的手臂扑了个空的事实。但是,面对照片或画中你的脸,你永远不能完全感到自在,我面对我的照片和画像也是如此。像神话中的那喀索斯一样,我们都沉迷于自己的倒影,以至于无法意识到它有多么奇怪。如果你用手指圈出镜子或玻璃中映出的自己脸的轮廓,你会惊讶于它竟然这么小。当你用一根手指顶住镜子,使你感到惊奇的是它的前后颠倒而不是左右颠倒。指向前方的手指的映像会指向相反的方向,但指向右侧或左侧的手指方向并不会发生变化。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上下方向,镜子不能反转它们的方向。你觉得镜子颠倒了左右只是因为你将自己代入了图像中,把自己的脸换成了她的。她的左耳戴着你戴在右耳上的耳环,反之亦然。今晚或明天一早,在黄昏或黎明半明半暗的光线中,从夜梦中抽离的你,发现自己站在镜子前。你会做什么?是像善良的爱丽丝一样,试图穿过镜子遇见自己的映像?或者,想到自己留在我的视网膜或其他底片上的倩影,像邪恶皇后一样对镜子提问:“魔镜,我的欲望之镜,告诉我,谁是王国里最美丽的人?”哲学山脉迦勒底之水的发现(占星术)有谁不认识几个性格古怪(lunatico)或是热情开朗(gioviale),抑或令人欢欣(solare)的人?但又有谁真的相信是月亮(Luna)、木星(Giove)或太阳(Sole)曾经或正在影响着他们形成这般性格?更笼统地说,有谁相信行星与其他星星已经或正在对我们的生活和性格产生影响呢?相信这些的人如今肯定还存在着,至少从星座说与更全面的占星术之普及就能管窥一二。但观测天空来知晓地球之事是一个古老的习惯,起码在最初也有其前科学时代的道理。月球与主要行星其实是在天球的一条狭窄带中移动。这条狭窄带只在黄道上(太阳似乎围绕地球运转的那个平面)延伸了几度,它包含了12个星座,太阳看似会在一年中依次经过它们。为十二星座命名的也许是巴比伦人。这些名字是为了纪念在太阳经过该星座那段时间里发生的事件。比如,白羊座的时间与羔羊诞生的时间相符。金牛座,是人们使用公牛耕作的时间。天秤座,包含了一年一度的日夜等分日(秋分)。向后行走的“巨蟹”,代表着太阳的路径由上升转为下降的节点(夏至)。而摩羯座则与之相反,太阳重新开始在天空中如同山羊一样向上攀爬。诸如此类。似乎最先被分隔出的是金牛座、双子座、狮子座与天蝎座,因为它们最明亮,并且其形象已出现在一些可以上溯至公元前年的巴比伦遗迹上。接下来是白羊座和射手座。之后补充了巨蟹座、处女座、摩羯座、水瓶座和双鱼座。最后,原先的天蝎座被一分为二,由此诞生了天秤座。所以,完整的系统有12个星座,早在公元前年,巴比伦已经使用了这个系统。因为几乎所有的星座都以动物命名,所以整个系统就叫十二宫(zodiac,源自zōion,“动物”)。太阳依次经过的时间被称为星座(zodiacsigns),以同样的名称命名。白羊座被确定为年度周期的起点,因为它对应着春分时间。然而渐渐地,黄道十二星座原本坚实的天文学基础被附加了经不起推敲的占星术内涵。与天体运动与四季轮换相关的科学真知变得神秘深奥,而那些与人的生命与性格相关的假想人类学意义则占据了上风。公元前几个世纪,罗马确实遭到了一群占星师入侵。为了强调其美索不达米亚的出身,他们被称作迦勒底人(Chaldean)。他们一直活跃至尼禄时代才慢慢消亡。但占星术仍然牢牢掌握在江湖骗子手中,尽管在某些时候也有一些伟大的科学家沉沦其中。比如年,吉罗拉莫·卡尔达诺为爱丁堡大主教与英格兰国王编制了光明占星术(radiantastrology)。但由于大主教很快就被革命者绞死,而国王则于一年后死于结核病,科学家被迫立即返回意大利。伽利略也曾为了增加收入练习占星术,安德烈·阿尔比尼(AndreaAlbini)的《占星术与望远镜》(OroscopieCannocchiali)讲述了他的占星术实践。今天,出于很多原因,我们当然知道占星术不过是一种伪科学。首先,星座并不存在,它们只是一组组被人为结合起来的星星,只因为在我们眼中它们位置相邻,有相近的明亮度。其次,对于黄道星座的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sushisr.com/speegk/6009.html
- 上一篇文章: 侠骨柔情的留尼汪,硬汉温柔起来也是无法抗
- 下一篇文章: 塞班起,迪拜自由行起,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