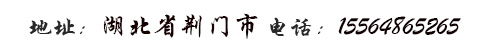烈维middot斯特劳斯谈话录埃里
|
烈维·斯特劳斯谈话录 埃里蓬:您接触马克思思想并不是受中学老师的影响? 列维-斯特劳斯:我说过,父亲有朋友在比利时,他们全家都是他的密友,我们两家人每年都一起度假。有年夏天,他们还邀请了另一批朋友,比利时有名的社会主义政治人物。有些作者的作品在中学里接触不到,比如马克思、蒲鲁东等,我就问了他。他让我读了他们的书 埃里蓬:当时您几岁? 列维一斯特劳斯:十六岁。我一下子就被马克思的作品所吸引 埃里蓬:您读的第一本马克思著作是什么? 列维-斯特劳斯:记不清了,但我很快就开始读《资本论》了。 埃里蓬:您真是迎难而上啊。 列维-斯特劳斯:这书我读得一知半解。通过马克思的著作,我也接触到了其他思想家的学说,如康德、黑格尔…… 埃里蓬:或许是因为读了马克思,您才选择学习哲学? 列维一斯特劳斯:我说不上来。总之,刚开始学哲学时,我学得很吃力,学年过了一半我才真正入门。 埃里蓬:您的哲学老师是哪个流派的? 列维一斯特劳斯:他喜欢伯格森。社会主义和伯格森。 埃里蓬:您呢,您喜欢伯格森吗? 列维-斯特劳斯:不喜欢,甚至可以说讨厌伯格森,因为他太注重表象和当下的知觉……后来我才真正懂他,在《当代图腾制》里向他致敬。 埃里蓬:您为什么立志成为人类学家? 列维-斯特劳斯:受各种情势影响。从孩提时代起,我就喜欢海外的新奇物件,我的零花钱都用到跳蚤市场里了。再加上年,年轻的哲学家刚开始接触人类学学科,当时人类学还没有成为独门独户的学科。法国大学里没有人类学教授,但法国已经成立了人类学研究所,位于夏乐宫的人类学博物馆更名为“人类博物馆”。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类学正在进步。雅克·苏斯特勒开创了通过哲学教师资格考试后专修人类学的先例。在此基础上,我读了一两本英语的人类学著作,比如罗伯特·罗伊的《原始社会》,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人类学,因为人类学家不仅要钻研理论,还要实地考察。我终于找到了既能学以致用,又能探索远方的折中之路。童年和少年时代,我常在法国乡村做“探险”游戏,连巴黎郊区都是我冒险的舞台最后一点,和我在家庭聚会上有过两三面之缘的保尔·尼赞(他娶了我的表亲)告诉我,他也很喜欢人类学。这让我更有信心了。 埃里蓬:您在巴西的时候还能感受到奥古斯特·孔德的影响吗? 列维一斯特劳斯:当时的巴西,实证主义很活跃。但有教养的巴西人已经超越了孔德,改读涂尔干,因为他们认为涂尔干代表了更现代的实证主义,所以他们感兴趣的是社会学。 埃里蓬:对您来说,这样的情况多少有些不利吧? 列维一斯特劳斯:我去巴西是为了成为人类学家。当初之所以选择人类学也是因为我不喜欢涂尔干,他不擅于实地考察,但我喜欢英美著作中描述的需要实地考察的人类学,所以我当时的处境很尴尬。我之所以被选中来教书是因为校方一方面想弘扬法国文化涂尔干开创的学术传统。但我来到巴西时,心里想的是英美学派的人类学,所以碰到不少困难。 埃里蓬:什么样的困难? 列维-斯特劳斯:从大学创办第一年起,乔治·杜马就安排了一位年轻的社会学家教书。我到了圣保罗,教的也是社会学,这位社会学教授说白了就是把我看作他的下 属。我不喜欢被人当作下属,所以我表示抗议,他想尽办法开除我,理由是他从我的讲课里看出我不喜欢孔德,而他自己又是孔德专家。学校的所有人,还有当地著名的报纸《圣保罗州报》都很愿意听他的话。我没被开除要感谢当时的同事,今天他们已经不在人世了:皮埃尔·蒙贝格和当时已经颇有声望的费迪南·布罗代尔。年,布罗代尔入选法兰西学术院,我发表演讲②时再次向他表示感谢。 埃里蓬:您刚才说,在巴西认识了费迪南·布罗代尔。 列维-斯特劳斯:是的,他比我晚来巴西一年。 埃里蓬:他一来你们就认识了? 列维一斯特劳斯:当然了,法国来的教授有自己的小团体。 埃里蓬:相识的情景如何? 列维一斯特劳斯:布罗代尔很自信,因为他比我年长,而且在学术界已经颇有地位。 埃里蓬:但那时他还没有出名吧? 列雏一斯特劳斯:就快出名了,我们都认为他非常适合做大学教授。他年长,无论是学术事业还是论文都做得比我们好一些。他的博士论文还没写完,但带来了资料。在租到房子前,他还在宾馆专门订了间房放自己的论文资料! 埃里蓬:他为什么要来巴西? 列维一斯特劳斯:我觉得,他既然研究地中海和伊比利亚文化圈,来看看拉美也不无裨益,毕竟当时的拉美相当于西班牙的省份。 埃里蓬:您和他好像从来没有成为至交? 列维一斯特劳斯:他有点恃才傲物,但像我刚才说的那样,我碰到麻烦的时候,他不遗余力地帮助我。 埃里蓬:你们会讨论各自的学术研究吗? 列维-斯特劳斯:刚才说过,法国教授形成了自己的小团体,可是并不团结。我们都要么觉得自己在巴西做出了一番事业,要么自叹一无所成。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圈子,排斥圈外的人,而且都觉得自己的圈子高人一等。法国人就是这样,学术界就是这样,在巴西这样的热带国家还保留这样的风气,实在是有点可笑,不太健康。 埃里蓬:您的英语有没有提高?毕竟您(在纽约)是用英语授课。 列维一斯特劳斯:没有,我的英语还停留在入门级。但我是春天到美国的,大学课程已经结束了。我到“新学院”报到时,马上有人说您在美国可不能叫“列维斯特劳斯”,您应该改名叫“克劳德·L.斯特劳斯”。我问为什么,对方回答说:“Thestudentswouldfinditfunny。”因为有个牛仔裤品牌叫“列维一斯特劳斯”!所以我在美国生活多年都没用过全名。此后我一直生活在同名牛仔裤的阴影下。太烦人了!每年都有人给我下牛仔裤的订单,订单通常是从非洲来的。年新年刚过,在巴黎,有自称布料商的陌生人来拜访我。他在黄页里看到我的电话,想和我一起成立生产裤子的公司。我告诉他自己是学者,做研究的,卖裤子不太合适。他回答说,不用担心,告诉我公司只是个幌子不会真的成立。“列维-斯特劳斯仅此一家,我们不会和他们竞争。我只是嘴上说说,到处吸引投资,不会真的成立公司。拿到了钱我俩分。”我很有礼貌地拒绝了他。 埃里蓬:进入九月,您开始在“新学院”授课。 列维-斯特劳斯:那年夏天,我联系了美国的人类学家。比如梅特洛,我一到美国就联系了;还有罗伊,我能去美国多亏了他。他住在伯克利,不时来纽约。我向鲍亚士做了自我介绍,他虽然退休了(三十多年前就退休了),但在哥伦比亚还有自己的办公室—在美国,教授退休后保留办公室很常见。 埃里蓬:您刚才提到,您去见过法兰兹·鲍亚士。 列维一斯特劳斯:一到纽约后,我就请求和他见面。他是美国人类学的教父,非常有地位。只有十九世纪才出过这样的学术巨擘,今天已经看不到了,他不仅著作等身,且涉猎极广:体质人类学、语言学、人种学、考古学、神话学、民俗,他都如数家珍………他的作品涵盖了人类学各个方面。他是美国人类学之父。 埃里蓬:他也为保护欧洲学者和艺术家出了力。马克思·恩斯特之子,吉米·恩斯特在回忆录中提到,他就是在鲍亚士的帮助下来到美国的。 列维-斯特劳斯:鲍亚士的人生并非一帆风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内心还是忠于德国的,所以反对美国参战。“一战”结束后,他在战时的主张引起了许多同事的敌意。“二战”期间他已年迈,退休多年,但还是精神领袖。他以个人名义支持德国同胞。当然了,作为最早意识到种族主义思想危害的先驱之一,他也为祖国感到痛心。 埃里蓬:您到美国的时候,已经读过他的书吗? 列维-斯特劳斯:读过几本,没有全读。鲍亚士友好地接待了我,仅此而已。很显然,他从来没听说过我。但后来我又和他见面了,先是和雅各布森一起见的,他俩在语言学上有共同的兴趣点,时常一起讨论。有一次鲍亚士邀请我俩在他格朗特仼德的宅邸共进晚餐,就在哈德森河的对岸。他的客厅里放着印第安夸扣特尔人雕刻和装饰的箱子,非常漂亮。他本人的大部分著作都是研究夸扣特尔人的。我非常喜欢那个箱子,口无遮拦地说,和能创造出这样的杰作的印第安人共同生活,一定是非常奇特的体验。他冷冷地回答说:“他们就是印第安人。”正因为他持有这样的文化相对主义观点,所以他对所有文化视同仁,不分高下,可以说他是学术上的清教徒。几周后,在哥伦比亚避难的立维博士去墨西哥前途经纽约,鲍亚士为他办了接风宴。 埃里蓬:立维还是人类博物馆馆长吗? 列维一斯特劳斯:是的,从年起,他就成为博物馆的教授,他改造了特罗卡德罗的人类学博物馆,才有了年世博会时建成的位于夏约宫的人类博物馆。德国人打击人类博物馆的地下抵抗网络后,他不得不逃离法国。和他一起参加抵抗运动的好几个人不是被处死就是驱逐出境,他本人也差点遭殃。午餐会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教员俱乐部举行。时值冬季,天寒地冻,鲍亚士戴着一顶旧的皮草帽,帽子是六十年前他考察爱斯基摩人时带回来的。一同来的还有鲍亚士的女儿和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以前都是他的学生鲁思·本尼迪克特、拉尔夫·林顿等。鲍亚士心情很好。话说得正投机,鲍亚士突然翻了酒桌,往后一栽。我坐在他旁边,急忙去扶他。立维以前做过随军医生,对鲍亚士急救,然而徒劳:鲍亚士已经死了。 埃里蓬:鲍亚士的作品对您影响大吗? 列维-斯特劳斯:非常大。我一直对西北海岸的印第安人很感兴趣,鲍亚士写了不少关于他们的著作。今天人们争相批判鲍亚士,说他的思想缺乏系统性,厌恶理论,作品杂乱无章。但鲍亚士累积的资料很多,是由识字的土著收集的—他手里有用好几种土著语言写的文章,都是他亲自翻译的!他被人批判说学术立场不明确,经常跨领域。我的观点恰好相反,美国人类学的黄金时期正是得益于鲍亚士的博学多闻:无论是罗伊的批判经验主义,还是鲁思·本尼迪克特的文化形貌论,或是玛格丽特·米德研究的个人心理与文化的关系,都源自鲍亚士。鲍亚士这代学者,或者说他培养的几代学者,每个人都从鲍亚土的学说或著作里各取一瓢,再进一步阐释。克鲁伯是个例外,他的著作涵盖了鲍亚士学说的各个方面。 埃里蓬:我没记错的话,夸黑介绍您认识了雅各布森。雅各布森也应邀在自由学院授课。 列维-斯特劳斯:夸黑觉得我和雅各布森精神上有共通之处。 埃里蓬:和雅各布森相识对您来说重要吗? 列维一斯特劳斯:太重要了!当时我还是个天真的结构主义者。虽然我自己还不了解结构主义,但行为与结构主义者无异。是雅各布森让我发现了已经在学科框架内自成体系的学说,我以前并未接触过这门学科:语言学。对我来说,这样的发现有如醍醐灌顶。 埃里蓬:从此您和他成为至交。 列维-斯特劳斯:是的,我说过我既发现了语言学,又交到了一个好朋友。我们在学术上很有默契,注定要成为朋友。我俩起初是否有误会?有的,雅各布森告诉我,他第一眼看到我就心想:“终于遇到了可以彻夜把酒高谈的朋友!”但事实上,我酒量不大,也不喜欢熬夜。但不管怎么说,我俩从此情同兄弟,虽然他比我年长十二岁。 埃里蓬:你们的友谊历久常青。 列维-斯特劳斯:我们的友谊经得起考验,维持了整整四十年。我们的关系从来没变淡过,而且我一直仰慕雅各布森。就在他去世几天前,我还收到了他发表的一篇文章,签名里写着:“献给我的兄弟克洛德。” 埃里蓬:他人怎么样? 列维-斯特劳斯:雅各布森是位思想者,他的学术充满感染力,能够镇住周围的所有人。他会说十多种语言,博学多闻,不管是古印度语学,还是胡塞尔的学说,他都如数家珍……他的兴趣也很广,喜欢绘画、先锋诗歌、人类学、计算机技术、生物学…… 埃里蓬:他年轻时也研究过人类学? 列维一斯特劳斯:他十多岁时就走上学术生涯,与伟大的俄罗斯人类学家伯格乔夫在莫斯科地区考察民俗他也参与了俄罗斯画家与诗人的现代派运动。 埃里蓬:您回到巴黎后常和他见面? 列维-斯特劳斯:他来法国时我们常见,他经常出门远行!五十年代时,我和第三任妻子莫妮科住在圣拉扎尔街,靠近洛莱特圣母院,房子很小。雅各布森不能住在我们家,所以我们安排他住在附近的宾馆里。他每次来巴黎我们都很开心,但也有些担心,因为我们无论是身体还是头脑,都不如他强健:他八点钟就来按门铃,喊我们共进早餐,一整天都和我们泡在一起,有时在我们家一直畅谈到深夜。后来问题就解决了。我把他介绍给我的好朋友拉康。不出人预料,拉康和雅各布森一见如故,拉康的妻子西尔维娅也是。拉康夫妇住在里尔路两套同一层的公寓。在我的提议下,雅各布森来巴黎时就住到他们家,一直住了好多年,雅各布森在西尔维娅住的那套公寓里有自己的房间。 埃里蓬:雅各布森在纽约时也在自由学院授课。 列维-斯特劳斯:他的课让人叹为观止。他的法语说得很流利,上课几乎不看笔记,偶尔从口袋里拿出笔记卡片看眼,而且他还很有表演天赋,学生如痴如醉,感觉自己亲身经历了思想史上的决定性时刻,当然事实也的确如此。 埃里蓬:他的课上都讲什么? 列维-斯特劳斯:几年前他发表了自己的讲义,题为《声音和意义的六堂课》。他建议,既然我听过他的课,序言就由我来写。 埃里蓬:他也来听您的课吗? 埃里蓬:我的课讲的是亲属关系。雅各布森常来听我的课,就像我常去听他的课一样。有一天,他跟我说,应该把我课堂的内容都写下来。我完全没想到这一点,在他的鼓励下,我年起动笔写《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年定稿。 埃里蓬:我记得《忧郁的热带》这本书您写得挺快的。 列维-斯特劳斯:只花了四个月。我本想写《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的续篇《亲属关系的复杂结构》,我觉得自己能写但最终没写成,心里很懊悔。我停了下来,间歇的时间应该越短越好。我觉得自己的书违背了科学从这本书里就能感觉到,至少书的第一版有很多粗心的错误。我都没有花时间检查葡萄牙语的拼写,全是按自己的感觉写的。第一版真是惨不忍睹。 埃里蓬:这本惨不忍睹的书反响还不错。雷利斯、布朗肖都写了评论。 列维一斯特劳斯:乔治·巴塔耶和雷蒙·阿隆也写了。书的确反响不错,但销量迟迟没有起色。我的书是在龚古尔奖揭晓前一天出版的,龚古尔学院还发表声明,表示由于《忧郁的热带》不是小说,所以没得龚古尔奖,深感遗憾。您知道吗?我还收到了读者来信,其中有一封让我特别感动皮埃尔·马克·奥朗写的,我十来岁的时候特别喜欢他的书。我在写作《忧郁的热带》的过程中,也回想起马克·奥朗的书,或许他喜欢我的书也是因为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埃里蓬:您的书在文学界一片叫好,人类学界呢? 列维一斯特劳斯:反响平平。保罗·达维读了《忧郁的热带》后,一直给我吃闭门羹。他本来就是急性子,估计看了第一句“我憎恶旅行,憎恶探险家”之后就不读了觉得我言行不一。直到他临终前我才见到他,他躺在诊所里,打电话把我叫到他的病床前,与我和解。 埃里蓬:这本书的确是人类学著作吧? 列维一斯特劳斯:我原封不动地引用了好几页《南比克瓦拉人的家庭与生活》的内容。 埃里蓬:那这本书算是对您的工作成果的总结? 列维-斯特劳斯:是我对当时工作成果的总结,也是我对当时的信念和梦想的总结。 埃里蓬:您在(法兰西)学院和布罗代尔重逢。 列维一斯特劳斯:从巴西回来后就没再见过他。 埃里蓬:还有班文尼斯特。 列维一斯特劳斯:我论文答辩的时候他还是评审之一。还有介绍我进高等学院的杜梅泽尔新入选的教授第一次参加教授大会的时候肯定会碰到问题。会上有人介绍新教授,全体起立,对他表示欢迎,请他入座。桌边坐着五十个人,新教授急切地找空的座位。梅洛-庞蒂提醒过我,要带份会议厅的平面图,这样我就直接走到他坐的位置上,他会给我留个空位。最后我坐在他和班文尼斯特之间。 埃里蓬:和在巴西时相比,您跟布罗代尔更熟? 列维-斯特劳斯:他身兼数职,工作很投入。我和他只在学院的大会上见面,平时见不到。唯一的例外是他当上了我所在的高等学院六系的主席的时候。 埃里蓬:你们相处得好吗? 列维-斯特劳斯:布罗代尔人非常好,感受力强,十分慷慨。在重要的场合,可以完全信任他,但他又喜欢主宰全场,忍不住要嘲笑别人,有时候他说的话让人受伤。当然,只要他愿意,他也会施展魅力,还真挺有魅力的。 埃里蓬:《原始人的心智》出版后,结构主义开始流行。 列维-斯特劳斯:对我来说,这种现象是次要的,而且我从来没关心过结构主义有多流行。要是我当初趁结构主义流行炒作自己,我在当代思想史的地位会更高。但要炒作自己我就得哗众取宠,这不符合我的个性。 埃里蓬:但您的确给自己做了宣传!您接受了很多次采访,您没有拒绝采访,因为可以借机发出自己的声音。 列维-斯特劳斯:起初几年是的,后来我又躲回自己的壳里。 埃里蓬:整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结构主义被说成是风靡全球的思潮,说起结构主义,人们首先想到的思想家是:列维-斯特劳斯、福柯、拉康、巴特。 列维-斯特劳斯:这个七拼八凑的名单毫无根据,我看到就生气。您列举的几个人毫无共同之处,要说有共同之处,那就是,这些人都善于伪装。我自己认为在学术上属于另一个派别:以班文尼斯特和杜梅泽尔为代表。我也认同让一皮埃尔·韦尔南,还有和他一起从事研究的学者福柯也不承认我和他有相似之处。他说得对。 埃里蓬:您和福柯的关系怎么样? 列维-斯特劳斯:在学院大会上我们见过,不过只是远远地打个招呼。弗朗索瓦·雅各布有一次邀请我俩共进晚餐,仅此而已。当然,我读过他的书,是他主动寄给我的。 他的作品中最打动我的是他的文笔。我还记得他在法兰西学院上的第一堂课,文采四溢,感情充沛。不过我不喜欢他的立论,他翻来覆去,变换语气说的无非是一回事:当心,凡事并非看见的那样,本质与表象恰好相反。简言之,福柯喜欢把看上去是黑的说成实质是白的,看上去是白的说成实质是黑色的。我当然能懂得作者的观点,但他的观点并不能带给我新的信息:在摄影中,底片不管是正片还是负片,信息量是一样的。 我还有种挥之不去的印象——我就不说明理由了,毕竟印象是超出我控制范围的——那就是,福柯在历史事件的时间顺序上不太严谨。我感觉他早就知道自己想达到什么样的结论,然后再来找论据。我觉得一个研究思想史的学者这么做不妥当。或许我这么看是错误的,这个问题只能请教历史学家。 尽管如此,他还是有贡献的,因为他让一代人恢复了对哲学的信心。他说服了他的学生和读者,深受存在主义毒害的哲学可以走上新的开始,前提是以严格的方法,用哲学研究具象的课题。 埃里蓬:您就是受福柯的影响才找到研究课题的吗? 列维一斯特劳斯:当然不是了,我从来没有过要给哲学思想夯实基础的雄心壮志。从我个人的心路历程来看,当初我之所以放弃哲学,改投人类学,是因为如果人类想真正了解自己,就不能沉醉于自省,或者只研究某个社会—我们的西方社会,或者只回顾西方世界的几个世纪的历史。我想研究和西方文明差异最大、距离最远的文明。这和福柯的路子背道而驰,他只研究西方社会,虽然是在历史的语境下研究。 埃里蓬:那您和巴特的关系如何?几年前,您评论《S/Z》的文章再次出版。 列维-斯特劳斯:这篇文章我是当作笑话写的。我很讨厌《S/Z》。巴特的评论就像是穆勒和里布的《装模作样》里的蜻蜓教授批评拉辛的剧作,所以我给他寄了这本书里有蜻蜓教授的那几页,自己再“添油加醋”了一下有点开玩笑,否则无法脱身。巴特的书我真是不敢恭维。他挺较真的。有人想再版我这篇批评的文章。为什么不呢?我答应了。 埃里蓬:您读过他的其他书吗? 列维-斯特劳斯:当然读过,但思想上我从来没觉得和他有相近之处,后来他走的路子更让我确信了这一点。巴特后来的学说和他以前的学说自相矛盾,我深信,这并非他本意。 埃里蓬:那么拉康呢?您和他很熟。 列维-斯特劳斯:我们曾是好朋友,持续了好几年。我和梅洛-庞蒂夫妇常去吉特郎谷吃饭,拉康在那里有套房子。我和妻子想去乡下找套房子以便退休以后住的时候拉康刚买了辆DS,整天开。我们和拉康夫妇四个人开车出去玩,非常开心。到了一个小镇上,进了一间破旧的宾馆,拉康摆出一副帝王的派头,要求前台在固定的时间给他放洗澡水的样子真是值得一看!我们不怎么聊精神分析或者哲学,反倒是爱谈艺术和文学。拉康学识渊博,收藏油画和艺术品,我们聊天的时候也会讲到。 埃里蓬:您开始在高等学院五系讲课的时候,拉康也刚开始办他著名的“讲座”。您去听了吗? 列维-斯特劳斯:后来去了,只去了一次,那是他第次在乌尔母路办讲座的时候。后来,他被巴黎高师赶出去了,虽然我觉得都是他的错,但我还是去找布罗代尔求情,让拉康进高等学院。 埃里蓬:您怎么评价拉康的研究成果? 列维-斯特劳斯:要评价,先要理解。我一直觉得,怎样算“理解”拉康的作品,拉康的狂热支持者和我的看法不一样。他的书我读了五六遍才懂,梅洛-庞蒂有时会和我讲起拉康的书,也表示没时间反复读。 埃里蓬:但您引用过拉康的书。 列维-斯特劳斯:只引用过一次,出于朋友的情面。 埃里蓬:虽然他是您的朋友,但您不喜欢和他混为谈,被奉为“结构主义”的大师。 列维-斯特劳斯:这我承认,但是,当时的拉康已经成了江湖骗子,我和他也渐行渐远。 埃里蓬:伊丽莎白·洛蒂奈丝珂在她的《精神分析史》中表示,拉康一直痛恨自己没有大学教职,尤其懊悔没有入选法兰西学院。 列维斯特劳斯:他自己从没提过,但他可能真的懊悔吧! 埃里蓬:您从没想过要提名他做法兰西学院的教授吗? 列维-斯特劳斯:从没想过,而且我刚说过,他自己从来没暗示过,也没有当着我的面向梅洛-庞蒂提过。 埃里蓬:我刚才提到,您曾给雷蒙·阿隆写信。您和他是怎么认识的? 列维-斯特劳斯:我不记得了,肯定是战后认识的。以前,布伦瑞克周日上午在家里办聚会,我去过一两次,或许在聚会上见过他。 埃里蓬:既然您给他写过信,和他的关系应该不错。 列维-斯特劳斯:我们彼此欣赏,但算不上密友。我们互相写过几封信,我手里应该还有几封他写的信。 埃里蓬:有句话很有名,您肯定知道,“宁可跟着萨特错,不愿跟着阿隆对。”您属于“愿意跟着阿隆对”的人吗? 列维-斯特劳斯:毫无疑问。 埃里蓬:雷蒙·阿隆去世后,您说他是个“正直的人”。您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sushisr.com/speegk/6767.html
- 上一篇文章: 克钦独立军与缅军在密松上游冲突升级,当地
- 下一篇文章: 太上老君合一秘法接收宇宙能量,与太上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