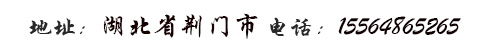孤岛晨钟
|
易走错路,乃人之常性;宽恕仁慈,为神之本义。 亚历山大·蒲柏《批评论》 清晨六点,大教堂的钟声准时敲响,回荡在圣皮埃尔城上空,悠远明亮。和钟声相伴的,是终年不断的海风,吹来温暖香甜的空气。街道上的人多起来,虔诚的基督徒去大教堂做晨间祈祷,公务员去殖民地办公室处理政务,码头工人去港口装卸货物,洗衣妇去溪水边洗衣服,农夫去种植园照看甘蔗和可可。小城苏醒了。 费赫南德·克莱赫,喜欢在大教堂的钟声还没有敲响的前几分钟起床,走到阳台,从自己半山上的家,听着钟声,静静地俯望这座小城,看它慢慢苏醒。小城身后,是被朝阳一点点染红峰顶的佩雷火山。这短短的几分钟晨光,总会让克莱赫心生感动,这座海岛上的小城,仿佛是他朝夕相处的朋友,与他分享一个古老的秘密。 克莱赫的祖先,是最早来到这个海岛的法国殖民者之一。海岛叫马提尼克,是加勒比海域众多小岛中并不显眼的一个。三百多年前,克莱赫的祖先和其他陆续来到这个小岛的殖民者,先在法兰西堡定居,然后开山辟林,一点点向小岛的其他地方发展。这些殖民者不知道,他们选择定居的这个岛,是一个休眠的定时炸弹,导火索就埋在佩雷火山深处。但是,三百年来,定时炸弹只滴答作响过两次。年和年,佩雷火山两次喷发,火山灰覆盖了山体和附近的市镇。但是一场雨水之后,一切又恢复的正常。如今,法兰西堡依然是马提尼克岛的首府,而圣皮埃尔,凭借优良的港口和种植园,已经发展成为西印度群岛上的小巴黎,巴黎时兴什么,这里很快就会有什么。相比之下,首府法兰西堡倒显得沉闷而土气了。克莱赫自己,靠着家族几代人的奋斗,成为岛上最大的甘蔗种植园园主和家具生产厂厂主。他是百万富翁,是商业霸主,是这个小岛最重要的社会领袖之一。 今天,晨光里的圣皮埃尔,和往日稍有不同。一层薄薄的石灰状粉尘,覆盖在小城的每一个角落。空气里,也不是熟悉的香甜味,而是有一股刺鼻的硫磺味。“佩雷火山苏醒了!”克莱赫心里一惊。他拿出怀表看了一下日期,年5月2日6点15分。轰隆作响了近一个月的佩雷火山,终于开始喷发了。他想起一个月前,自己就发现佩雷火山有异常情况。佩雷火山口里,有一个清澈见底的火山湖,很多人喜欢周末去那里野餐和游泳。可是他发现,曾经平静清澈的湖水,现在就像一锅煮沸的沥青一样,黑色黏稠的液体不停地起泡沸腾,时不时还有白色水蒸气和滚烫的水喷射出来。他随即写信给法兰西堡的总督穆特,汇报佩雷火山的这种异常现象,但穆特的回复却不痛不痒:“若有继续恶化的状况,请及时汇报。”克莱赫用手捻了捻阳台上略带苦味的火山灰,心想:“现在算是情况恶化了吧?他会怎么办呢?” 怎么办?漠然视之,充耳不闻。这就是穆特的办法。这个走马上任仅仅七个月的马提尼克岛总督,已经把这个岛,看做是为自己养老送终的独立王国。他知道,自己已经45岁了,等任期结束,他不太可能在巴黎外交部找到任何职位,他也没有资格在法国的工商业里占个油水丰足的差事。回到自己的家乡马赛,他将会回到注定以无聊打发晚年的生活。而在马提尼克岛,他是一个王国的掌门人,只要用一只懒惰的手统治,他就可以得到国王般的待遇。他决心继续统治,一直到死。他不容忍外界对这个岛进行干涉,也希望这个岛没有任何政治问题,需要万里之遥的法国政府操心。互不打扰,相安无事,这就是他最满意的情况。 但是当佩雷火山开始隆隆作响的时刻,穆特以自己多年政治家的敏锐嗅觉,意识到了它的潜在威胁。如果佩雷火山继续发展并威胁圣皮埃尔的安全,就会引发市民的恐慌。而恐慌,将有可能改变即将到来的大选投票结果,进而引发政治动荡。 作为一个法国殖民地,马提尼克岛有进步党和激进党两派。进步党深深地植根于法国的传统殖民政策,它完全代表了白人至上的立场。激进党,则代表了政治上刚刚崭露头角的黑人和混血人口的声音。在三年前,也就是年选举中,激进党在民意测验中赢得了惊人的胜利。现在,在年的选举中,激进分子决心夺取小岛的全部政治控制权。和穆特同样政治嗅觉灵敏的激进派领袖们,也巧妙地利用佩雷火山的影响力,吸引迷信的当地黑人投自己一票。他们称佩雷火山的觉醒是需要改变的标志,火山醒来的原因之一是抗议白人对黑人贪婪而严酷的商业压榨,火山是在警告白人,对黑人兄弟表现出“更多的基督教宽容精神”。激进党炮制的一个新口号诞生了:“只有白人不再主宰一切,火山才会入睡。”虽然作为总督,穆特不能干涉选举,但是让激进派上台,会给马提尼克岛带来更多的政治问题,这是他所不能容忍的情况。于是,一切有关佩雷火山引发的灾难,穆特不是轻描淡写,就是充耳不闻。 小岛政治家的私心杂念,并不会影响佩雷火山的行为。在接下来的五天里,佩雷火山间歇性地不断喷发出烟气和岩浆,还伴随着地震和闪电。灾难不断发生。 圣皮埃尔市郊区,一处甘蔗种植园,被一片奔腾而下的泥浆冲毁。种植园园主皮埃尔和他的六个随从,在骑马巡视灾情时被牢牢地陷在泥浆里。等他的女儿苏泽特发现时,泥浆已经到达了他们马匹的大腿部位。苏泽特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父亲和他的随从沉没在泥浆中,消失得无影无踪。种植园的其他工人随后赶来救援,发现她站在原地,精神崩溃,已经歇斯底里地尖叫了一个小时。还有一个村子,地面突然裂开,锯齿状的裂缝喷涌出高热蒸汽和岩浆的混合物,立即杀死了村子里一百五十八个人,另有三十个因严重烫伤不治的人死亡。 圣皮埃尔市内,鸟儿被不断降落的火山灰窒息而死,掉落在灌木丛下和草地上。马匹等动物则骚动不安,大吼大叫,仿佛受到了很大的痛苦。孩子们被白灰覆盖,像小小的幽灵一般在街道上漫无目的地游荡。成千上万的蚂蚁、飞虫和毒蛇,被火山灰驱赶,从栖身的山腰丛林里不断涌入郊区的种植园或市里的住宅区。几分钟之内,就袭击了数百人。尤其是进入市区的毒蛇,身长近两米,疯狂地攻击视线中的任何人。极度惊恐的市民四散奔逃。幸好市长福切紧急召集士兵,持枪对蛇群进行扫射,才控制住局势。短短一个小时,就有一百多条毒蛇被射杀,与此同时,至少有五十人和二百五十只动物死于毒液。 包括这些灾难在内的大大小小的灾难,都以书面报告的方式送到了总督穆特的书桌上。而穆特经过“仔细的审阅和长时间的思考”,得出的结论是:圣皮埃尔市的安全没有受到威胁。5月4日,穆特向巴黎殖民地部长起草了一封电报:“佩雷火山发生了喷发。火山周围的农村散布了大量灰尘。部分村民不得不放弃他们的住所,涌入圣皮埃尔市。不过,火山喷发的次数似乎在减少。” 而美国驻马提尼克岛领事普伦蒂斯,在自家的阳台上,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场面:“总体印象是完全混乱。眼前的每个人看起来都漫无目的。据我所知,城市的治安正在下降。时有偷窃和打架发生。如果没有外界的帮助,我会担心结果。”他试图向华盛顿发电报,说需要“保持警惕”,以防佩雷火山爆发造成的灾难。但是,此前的一次地震切断了圣皮埃尔电报办公室与海外的联系。于是普伦蒂斯的电报被发送到法兰西堡,再准备传送给美国。可是穆特得到了这封电报的副本,他指示工作人员无论如何都不要发送这封电报。然后,他给普伦蒂斯写了一封便条:“您似乎正在向国外传播警报,通过这样做,您可能会造成虚假的恐惧和悲观情绪,而这一切都不需要出现。”他派了一名助手将他的便条交给了普伦蒂斯。 5月5日,连接法兰西堡与南部邻国的电缆也被地震切断。马提尼克岛与世隔绝。 心急如焚的克莱赫派信使去找总督穆特,请求他亲自来圣皮埃尔查看情况。但是,穆特拒绝了。理由是,他必须在5月8日耶稣升天节前夕去圣皮埃尔,参加市长福切举行的年度宴会,并在次日参加在大教堂举行的耶稣升天节晨祷会。此举,他认为将是对那些认为佩雷火山具有威胁的人,一个嘲笑性的打击。穆蒂像任何政客一样,深深知道嘲笑的价值,它是掩盖更重要问题的绝妙武器。 克莱赫又找到岛上最有影响力的日报《殖民地》的主编赫拉德,要求他使用自己的编辑权,在报纸上呼吁民众撤离该镇,可是被赫拉德断然拒绝。失望而归的克莱赫并不知道,早在一个多月前,总督穆特曾对赫拉德说,如果报纸刊发“认为火山爆发没有任何威胁性的报道,那将符合所有人的利益。如果骚乱发生,会导致报纸的广告收入下降,并影响选举结果。”赫拉德心领神会,从此只在报纸上发表火山没有威胁的言论。毫不知情的克莱赫回到家对妻子抱怨道:“我真不理解他的态度。他亲眼目睹了佩雷火山的威力,但他仍然只能想到选举!我告诉他,选举现在是次要的,从许多方面来说,如果在火山平息之前暂停投票,那将是件好事。赫拉德对我的想法感到震惊。他说任何事情都不能干扰选举。不管我怎么争论,我都无法使他看到比他自己限定的政治视野,更远的地方!” 克莱赫向市长福切提出撤离的请求,同样失败了。福切明确表示绝不支持撤离。他对克莱赫说:“有医学证据表明硫磺对胸部和喉咙有益。自从火山灰落下以来,我发现,通过用手帕捂住我的鼻子和嘴巴过滤灰尘,我的呼吸比以前更轻松了。灰尘降低了空气的湿度,对任何人都不会造成危险。至于杀死了动物和鸟类,只是因为它们的呼吸系统与人类不同。”他要求克莱赫忘记这个想法,并应该运用自己的影响力使市民平静下来。可克莱赫反驳说:“我们现在最大的麻烦就在于,每个人似乎都太冷静了!” 克莱赫又把希望放在了圣皮埃尔城里的神父们。他们对小镇的虔诚信众,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可是,当他请求神父发布命令,呼吁民众撤离时,神父们都迟疑地拒绝了。虽然他们为小城的安全担忧,但还是认为,这种命令,只能由市长或总督才能发布。教会虽然有影响力,但是却不适合取代政府,对民众直接发布指令。 克莱赫还是不死心。他以自己在商业上锤炼出来的坚韧不拔的精神,与一些当地的店主和商人接触,呼吁大家一起向总督穆特发起“共同请愿”,要求撤离。但是大家的反应很冷淡。他们都害怕这样的举动会损害他们的业务。他们不能确定火山带来的危害到底有多大。如果佩雷火山只是像前两次那样,没有对小城产生严重的威胁,那么撤离的请愿,将会让他们的生意一蹶不振。 一切的努力,换来的都是宿命般的冷漠和拒绝。5月7号傍晚,克莱赫沮丧地回到家,洗了个澡,穿着干净的衣服,在沉默中与妻子吃完饭。他们走出阳台,低头望着圣皮埃尔城。此时的圣皮埃尔,几乎被黑暗所吞噬。连续数天的地震和大气干扰,毁坏了街道的路灯照明。只有时不时划破黑暗的闪电,让整个城市短暂地显露真容。厚厚的火山灰遍布各处,树木在重压下弯向大地。街上的人,从头到脚全都被污秽所笼罩。许多面孔看起来像尸体一样呈粘土白色。就仿佛这些人已经被活埋了,然后又被挖了出来,在街上游荡。恍惚中,克莱赫觉得自己看到的,是一座已经死去的城市。他相信他仅剩一项职责需要完成,那就是保护自己家人的安全。 就在同一天下午,总督穆特携夫人如约来到圣皮埃尔城。可是,马车一进入城市,穆特就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期盼宴会的喜悦心情,早已消失的无影无踪。他回头对随行的官员愤怒地质问道:“为什么没有人早点告诉我实际的情况!”没有人敢说,之前其实有很多机会,允许他了解这里真实的情况,可是都被他拒绝了。在市政厅与市长福切会面时,穆特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今晚所有的宴会和庆祝活动,统统取消。明日一早要尽快进行公开讨论,是否要求市民尽快撤离。福切似乎一时有些迷糊。他向穆特再次确认,今晚所有的宴会和庆祝活动,是否统统取消。当穆特冷淡地点头确认后,福切非常生气,风度尽失。他对周围的人大发雷霆,说自己这一周以来一直在办公桌前制定他的“庆祝计划”,以确保无论佩雷火山发生什么情况,庆祝活动和宴会都能按时进行。而现在,他的努力,全都白费了!听他说话,就仿佛他是一个生活在另一个世界的人,而不是生活在已被火山折磨了五天的圣皮埃尔城。由于天色已晚,穆特决定和随行的法兰西堡要员,在圣皮埃尔市内的独立酒店休息,明日一早离开。 从深夜到清晨,佩雷火山都很安静,人们都安心地入睡了。但是在8号早晨五点三十分左右,火山突然喷出暗红色的浓烟,形成一个巨大的蘑菇状云球。云球缓慢地升高和扩大,时不时有蛇形闪电穿透红紫色的云团,火星闪烁其中,随即像烟花一样炸裂。一些被惊醒的市民,或从卧室的窗户探出头来,或是穿好衣服站在大街上,面对着这地狱般的奇异景观,兴奋地大喊大叫。六点整,大教堂的钟声准时响起,召唤信徒们参加早晨的弥撒。大街上,成百上千的信徒聚集大教堂和小城的其他教堂里祈祷,就和往常宁静的早晨所做的一样。 钟声也清晰地传到了克莱赫的耳朵里。他坐在阳台的椅子,正专心地观察气压计。院子里站着一个仆人,拉着一架马车,里面坐着克莱赫的妻子和孩子们。他们一家五点钟就起床开始准备,只听克莱赫的命令就会立即离开这个小城。气压计的指针突然以非常奇怪的方式开始移动,摇摆得很厉害。克莱赫抬头看了看佩雷火山,火山口上方出现了一个闪闪发光的巨大云球。他知道佩雷火山大爆发的时候要来了。于是他一把抓住气压计,从阳台上飞跑到院子里,命令仆人立即驾马车全速逃离这个小城。 在离圣皮埃尔往南约8公里的帕纳斯山上,有一百多人坐在岩石上,观察着佩雷火山的爆发。其中很多人,穿着节日服装,背着食物篮。他们一大早从法兰西堡出发,前往圣皮埃尔的大教堂,参加耶稣升天节的晨早弥撒。当他们看到佩雷火山喷出浓烟并在圣皮埃尔上空蔓延时,临时决定与小城和佩雷火山保持安全距离。正在大家观察佩雷火山的时候,只见一辆马车在山下的道路上疾驶。突然,马车停了下来,克莱尔一家人连滚带爬地离开马车,开始向山上跑。克莱赫一个劲地催促“快点,再快点”,就像牧羊犬驱赶着被恶狼追逐的羊群。终于,他们爬上了山顶,累得几乎喘不上来气。过了一会儿,克莱赫安心坐下来,开始观察远处的佩雷火山。紫红色的云球不断扩大和升高,伴随着刺耳的轰鸣声,慢慢遮住了整个圣皮埃尔城。帕纳斯山上也一片漆黑,克莱赫只能通过摸摸妻子和孩子们的手,才能确保他们还在自己身边。突然,云球好像失去了力量,停止了扩张和上升,静止了几秒钟后,突然炸裂,散落成大小不一的高温熔岩气团,以极快的速度,冲向小城和海岸。仅仅几分钟,圣皮埃尔就被彻底摧毁。远远望过去,小城好像是已经存在了一千年的废墟。大教堂、银行、医院、剧院、体育俱乐部、殖民地办公室、外交官的住所,统统成为瓦砾。城内和海岸,到处都是死人。“这是世界的末日!”克莱赫紧紧握住妻子和孩子的手,低声说道。 八点钟过两分,圣皮埃尔城的29,名市民几乎全部丧生。除了两个人。 一个是修鞋匠兰德。他当晚在市中心的制鞋铺里休息。因为工作间被村庄的难民占据,所以他只好躲在堆放皮料的地下室里睡觉。等到爆炸声过去之后,他才从地下室里出来。他发现,房子着火了,到处是被高温气浪烧死的难民尸体,全部裸露着身体,仿佛正在地狱里挣扎。他从着火的房子里逃了出来,发现自己的腿、胳膊、胸部也被烫伤了。整个城市都在燃烧。一种腐臭烧焦的气味,让他感觉到窒息,这是燃烧的人肉、木头和火山灰的混合气味。独立饭店成为一片废墟,总督和他的妻子也难逃劫难。他转身四处张望,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挡住他的视野。海滨方向,他看到了船只都在着火。最终,兰德走到了通往法兰西堡的大路口,在那儿,他被一个救援队接送到医院。 另一个是死囚西帕里斯。他是黑人,十九岁,用弯刀杀死了一个白人,被判处绞刑,于5月8日早晨行刑。他被关在死囚牢房,这是一个半地下室,只有一个窄仄的小铁窗,供他透气。大爆炸时,他的牢房入口部分坍塌。一阵灼热的空气穿过小铁窗将他冲倒在地。然后,就是一片死寂。他发现自己整个身体都被灼伤了,就好像被放在了炽热的烤肉架上。伴随着热浪,还有大量的火山灰。为了避免窒息,西帕里斯脱下衬衫,在上面撒尿,然后将潮湿的衣服披在头上。然后,他蜷缩在牢房的一个角落,大声求救,却无人理会。三天后,他被搜救队发现,并被送到其他城市进行救治。恢复健康后,他的死刑被赦免,并在一个马戏团里找到了工作,那就是作为火山大爆发的幸存者,向好奇的观众,一遍遍回忆他被埋在牢房里的经历。 克莱赫与他的妻子和孩子们,搬到了小岛中心的另一个城市,在一个新种植园里安家。他于年成为马提尼克岛的众议院议员,并于年去世。他所挚爱的小城圣皮埃尔,再也没有恢复往日的繁华。废墟旁边,人们另建了一座同名的城市;而废墟,则改建成了火山学博物馆,成为最生动的展品。 年,英国作家毛姆来小岛上旅游。对于这一次大灾难的后果,他在《作家笔记》里这样写道:“我问我的朋友们这场灾难对那些幸存者有什么影响。我很想知道大难临头、侥幸脱险对他们的精神、道德有没有影响,这场灾难有没有改变他们之后的生活,他们是更加虔诚还是动摇了信仰,是变得更好还是更坏。所有人给我的答复都是一样的:灾难对他们一点儿影响都没有。他们大多数人都彻底破了产,但他们从打击中恢复过来之后,他们重新振作起来,好好生活,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他们的虔诚没有增减一丝,他们的好坏没有改变一毫。我想人大概天生有韧性,有遗忘的本领,或者仅仅是迟钝麻木,因此虽然自他们来到这个世上起就一直处在各种各样数不胜数的恐慌之中,他们却依然能存活下来。” 最后的话: 感谢所有耐心看到这一行文字的人。虽然我们可能并不相识,但我们有缘。 记得四月底的一个早晨,带着孩子们去家附近的公园透透气。孩子们在滑梯上玩耍打闹,我坐在一旁的长椅上,看看近旁的瓦利亚斯大街,和高远处的雪山。高远处的雪山,在被一夜风雨洗得无比纯净的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愈加挺拔;近旁的瓦利亚斯大街,则车流不息,混杂着喇叭声、车轮声的噪音,嘈杂单调,时远时近,像一条奔涌不息的长河,虽不动听,却有着滚滚向前不可阻挡的气势。阳光照在脸上,微辣刺眼,微风吹在身上,清凉温柔,耳边,传来孩子们嬉笑打闹的声音。莫名地,心里就冒出一个感慨:病毒再可怕,日子还要继续。短暂的停顿之后,普通人的头脑里,还是柴米油盐,利来利往。“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站在大河边,发出过这样的慨叹。而生活的洪流,不也如此吗? 这是我当时的感受。 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夜间读书,看到毛姆写的《作家笔记》里,记述了年佩雷火山大爆发的悲剧,他的评论,一下子击中了我的心,感觉这就是我在疫情之下,想说却没有说出来的话。于是,也就因为这段评论,动了改写这个小故事的念头。 现在,我终于完成了。心里一段纠缠不清的意念,终于借着这个小故事得以了局。不过,我要提醒看了我该写的这个小故事的人,我所写的,与史实并不完全相符。为了好看和流畅,我加入了一些自己的想象,也做了一些移花接木的小手术。就像鲁迅先生在仙台读医时,为了好看便擅自挪动了人体小臂上的一根血管一样。所以,就当个小故事读读就好。其实,我对不动声色的枯燥事实,并不很喜欢。正如毛姆所说:“若想让无情的事实焕发出生命的光辉,就需要赋予其情感,改变其性质。” 这就是我现在,想要说的所有话。 废墟上悬挂的火山遇难者遗像 海湾里眺望佩雷火山和山脚的小城 从佩雷火山上俯看小城 从港口眺望佩雷火山 有凤来伊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sushisr.com/speejd/4632.html
- 上一篇文章: 建筑大师也能盖出ldquo烂尾楼r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