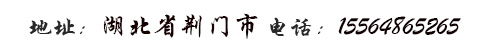从马赛到凤凰城带着对瘟疫的思考,我走过这
|
文|云泥 1 去年十二月四日,我乘飞机抵达法国马赛,比原定的日期早到一天。原因是为了避开第二天开始的法国交通系统工人大罢工。法国同事皮埃尔在电话里郑重其事地提醒我——“这次罢工抗议政府最新的退休政策,非同小可,铁路、公交车,全都要瘫痪。你最好早点来,要不然就等罢工结束——只有上帝知道那是什么时候。” 这是我第二次去马赛。每次去都要改机票。 上一次来马赛是二零一六年。那一次法国没有罢工,却更加不平静。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巴黎发生了一系列恐怖事件。在富有中国建筑元素的巴塔克兰(Bataclan)剧院,八十九名正在观赏“死鹰”乐队表演的观众被ISIS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枪杀。在距离剧院不到两公里的另外四个地点,几乎同时发生了爆炸,死亡人数总计一百三十人。 消息传到美国时,有一班从纽约飞往巴黎的飞机因此在空中转弯,重新回到肯尼迪机场。我的机票是第二天的同一架航班,必须改。 巴黎巴塔克兰剧院/图片来源于网络 过了五个月,我来到了马赛。全法国惊魂未定,仍处于高度警戒状态,公共场所可见荷抢巡逻的士兵。一个周末,我去了位于市中心的马赛历史博物馆,里面观众寥寥,数量只比博物馆外把守的士兵多一点点。 公元前六百多年,希腊人在马赛建立了贸易港。时至今日,这里仍旧商贾云集,是法国,也是地中海地区最大的商用港口。在博物馆的一层,我见到很多底部呈锥形的一人多高大土罐。希腊人发明的这种器皿在船运中有很多好处——两头都细的土罐首尾相互交错,增加了空间利用率;卸载时纺锤形瓶身容易滚动;底部做成内里厚实而外部尖细的形状,比平底容器更耐颠簸。 希腊人发明的尖底瓶/图片来源于网络 博物馆二层很大一片区域,是关于马赛的瘟疫史。 人来人往的繁华港口,细菌和病毒也在这里汇集传播。以鼠疫为例,从尤里斯凯撒的高卢战争起,马赛历史上有记载的鼠疫爆发有二十二次。吞噬了欧洲几乎一半人口的黑死病之后,一五八零年,马赛开始建立严密的卫生防疫系统,试图控制疾病的未来传播。马赛市议会设立了卫生委员会,该委员会的成员从市议会及医生中严格选拔。卫生委员会还负责医生的资格鉴定,向公民提供有信誉的医生名单。医院在此期间建成,并配备了全职的医生和护士。 对于外来的船舶,卫生委员会建立了三级防疫隔离系统。他们仔细查看船长的日志,其中记录了该船登陆的每个城市,将其与整个地中海的城市总清单进行核对。当前瘟疫发生的地点,无论谣言与否,都特别标注在城市总清单上面。最后根据检查结果,确定该艘船舶的健康级别,及其货物进入城市的日程。 没有任何疾病迹象的船只即通过了首级测试。假如该船的行程中包含有瘟疫发生的城市,则该船将被送往位于马赛港口以外的第二级隔离区,隔离至少十八天。对于暂无症状但高度可疑的船员和乘客,他们将被送往第三级隔离区,该隔离区建在马赛港口海岸附近的一个岛上。第三级隔离人员被要求在那里等待五十至六十天,以查看他们是否出现了鼠疫的迹象。 隔离区的标准是通风良好,有清洁用水。只有通过了三级考察的船只,才能最终进入马赛港。 然而在一七二零年。一只来自中亚的商船大圣安图望号,使这一切努力看上去比飞蛾的翅膀还要脆弱。这艘船经过当时爆发鼠疫的塞浦路斯,途中一名土耳其乘客死后,数名船员包括船上的医生也相继死去。到达马赛港后,根据三级隔离健康检查标准,这艘船应当进入最高级别隔离。当时市内有商人急需这艘船上装运的棉花和丝绸,他们计划把这些货物及时运到一个博览会上去销售。商人动用权势,强迫港口取消隔绝措施。大圣安图望号长驱直入。 仅仅几天之后,市内就爆发了瘟疫。医院爆满。万人坑很快挖成,但远远赶不上被填满的速度。在城市周围死尸堆积成山。为了阻止瘟疫蔓延,法国下令隔绝马赛和普罗旺斯的其它地区。为了保证隔绝,市郊建起一堵“鼠疫墙”。这堵墙是用石头造的,高两米,墙内有卫兵日夜把守。违反隔离命令的人一律处死。 法国普罗旺斯地区的“鼠疫墙”/图片来源于网络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到一七二二年为止,马赛的九万居民中有五万丧生。 博物馆展出的历史令人惊悚,残山剩水已逾三百载。在二零一六年,瘟疫似乎离我很远。尽管当时西非爆发了自埃博拉病毒被发现以来最大的疫情,美国也有人在旅行中感染,但是关于埃博拉的新闻都被我迟钝地忽略过去了。因为不得不来法国出差,我对于恐怖主义的动向更为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sushisr.com/speejd/6027.html
- 上一篇文章: 各国护照全球排名新加坡护照全球第二
- 下一篇文章: 三年两任诺贝尔奖得主专业超牛剑巴黎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