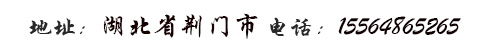圣路易时期的加冕程序年加冕礼仪
|
白癜风病能治愈吗 http://www.wxlianghong.com/ JacquesLeGoff,ACoronationProgramfortheAgeofSaint-Louis:TheOrdoof.inCoronations:MedievalandEarlyModernMonarchicRitual,ed.JanosBak,pp.46-58. 圣路易时期的加冕程序——年加冕礼仪书 雅克·勒高夫 (纪念皮埃尔·费农PierreFénot) 这篇文章讨论的是保存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拉丁区编号的一份档案,其中包含了非常重要的仪式信息。正如前言中提到的,在我们专门讨论中世纪仪式动作和仪式系统问题的研讨会上,我们作为一个团队对这份手稿进行研究,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包含了对加冕仪式的描述以及一系列相关的图像。遗憾的是,本应是我们的同事皮埃尔·费农(PierreFénot)所作贡献的部分永远也无法书写下来:几个月前,他被一种残酷的疾病击倒;我们为了纪念他而撰写了这篇文章。 让-克劳德·波恩(Jean-ClaudeBonne)将会讨论这份加冕礼仪书的文本及对我们的启示,他会提供一份文献学的分析,这也是我们的兴趣所在。我的研究强调手稿在形式、内容和思想上的统一,思想显然是所有其他因素的基础。这种统一反映了在圣路易统治下的法兰西王国实现的王室和教会权力之间不稳定的平衡,这对君主制和教会都有利,而这本加冕礼仪书就是一个主要的象征性证据。 对于这份手稿的创作时间和地点我们没有什么新的发现。尽管其插画的风格可以明显地确认为巴黎风格,正如罗伯特·班纳和弗朗索瓦·阿夫里尔(RobertBrannerandFran?oisAvril)在他们的研究中所指出,这份手稿在兰斯存放了很多个世纪,我们可以就此认为它就是在那里制作的。它的年代也很大程度上依据于插画判断。因为在年的第四次拉特兰大公会议(theFourthLateranConference)在《兰斯加冕礼仪书》中有过描绘,因此这本加冕礼仪书一定是在那之后制作的。弗朗索瓦·阿夫里尔作为十三十四手抄本研究的专家将它的制作年代划定在了年,我们接受了这一日期,理查德·杰克逊(RichardA.Jackson)也是。另外,这本书是为马恩河沙隆(Chalons-sur-Marne)的主教、兰斯大主教以及教会贵族们所制作的,但是根据勒罗凯(Leroquais)的研究,这不可能是沙隆教堂圣礼书的一部分,让-克劳德·波恩会在下一篇文章中给出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结论。尽管我们最初由于它只存在于沙隆教区的圣礼书中而称它为“沙隆加冕圣礼书”(theordoofChalons),但是我们现在更认可杰克逊的称谓:“年加冕圣礼书”(theordoof)。戈德佛洛伊的“路易八世加冕礼仪书”(OrdoofLouisVIII)和施拉姆的“编撰本”(Compilationof)如今都随着研究的进展被推翻。 正如理查德·杰克逊近来在他的作品《国王万岁!》中所说,大约有三种文献可以告知我们加冕仪式的情况:加冕礼仪书(ordos),即为国王祝圣加冕仪式所书写的礼拜仪式、祷文、赞美诗以及回应诗;目录(directories),即规范仪式过程中应该做什么的流程性文件;最后就是对于仪式有所记录的叙述性文献(narrativerecords)。《年加冕礼仪书》(Paris,B.N.,ms.lat.)与稍早的文本之间有着一定联系,其指导思想很可能可以追溯到圣路易统治的初年。那个文本,也就是所谓的《兰斯加冕礼仪书》(实际上是一个目录),尽管它很简短,却是一个重要的证据,因为我们发现在它里面最早提到了仪式的某些革新和一些法兰西君主同样也出现在我们研究的这份抄本里。这份手抄本将礼拜仪式添加了进去,通过对《兰斯书》的增补成为了一本真正的加冕礼仪书。《年加冕礼仪书》直接传承自《西法兰克加冕圣礼书》(WesternFrankishOrdines),其形式上在很多地方同时传承了中世纪早期盎格鲁-撒克逊圣礼书和欧洲大陆圣礼书的风格。我们把它看作一份档案文献,正如施拉姆所说的,一份汇编,一份文献,它不仅标志着一场仪式演变的一个阶段,而且还为我们研究后来其他仪式的发展提供了线索。 杰克逊还提醒了我们另一条重要的规则:除非有明确的证据,否则加冕礼仪书不应该与任何特定国王的实际加冕情况联系得太紧密。《年加冕礼仪书》可能从没有作为一场加冕仪式的指定指导方案。它当然没有被用于年的路易八世或年的圣路易的加冕仪式,但它很可能受到了这些仪式的影响。它在年腓力三世的加冕仪式上也未必有过使用,因为当时已经出现了《最后的直系卡佩加冕礼仪书》(thelastCapetianOrdo);然而,这份加冕礼仪书和它包含的思想对此后许多法国君主的加冕仪式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表达了一种仪式的基本程序,甚至被写进了《君主之鉴》(‘themirrorfortheprinces’)。 我对这份文献的讨论,将会围绕着两个观点展开。首先,仪式的结构应当被解读为一场特定仪式的展示。我更愿意把加冕仪式称作一场“过渡仪式”(ritedupassage)而不是简单的“就职典礼”(inauguration),当然它显然也是(因此这与拉尔夫·基塞、杰内特·尼尔森、萨拉·汉利对于梅耶·福特斯、克利夫德·格尔茨研究的引用也是相关的)。我的第二个观点是,这场仪式的两个主角,国王与主教——分别代表了王权与教权——利用了这场仪式来建立他们之间的平衡,而这种平衡在加冕结束后将会向国王倾斜。 首先,让我们讨论一下这场“过渡仪式”的要素:主题、地点、时间和程序。谁是仪式的主角?毫无疑问,这个主角肯定是国王,他在这场仪式中从一种身份过渡到了另一个。(当然,在这本加冕礼仪书的最后也提到了王后的加冕仪式,虽然国王是仪式的主角,但在中世纪的法国,正常的加冕礼适用于一对夫妇,也就是王后和未来国王的母亲。) 在仪式开始的时候,国王已经是国王了,但还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国王。当他到达兰斯时,国王就是国王是因为他已经满足了三个条件中的两个。首先,他是被上帝选中之人。这一点在加冕礼仪书的开篇,两名主教前往国王的寝宫迎接国王时颂唱的祷文中就已经明确:OmnipotenssempiterneDeus,quifamulumtuumN.regnifastigiodignatusessublimare....(在上帝指引之下来迎接您);当国王进入到教堂之时,赞美诗Dominesalvumfacregem…(上帝选择了我们的国王)开始颂唱。第二点,继承王位的先天继承权力,这在十三世纪时是必要的,只在兰斯大主教为国王加冕的过程中有所提及:Staetretinelocumamodoquemhucusquepaternasuccessionetenuistihaereditarioiuretibidelegatum.在这段话之后加上了一句强调国王选举的神圣性的文字:perauctoritatemDeiomnipotentis.然而只有通过这场仪式完成第三步,才能让王子成为真正的国王。在国王的涂油仪式中,主教会颂唱祷文ungoteinregem,在这里“in”显然是一个宾格,不仅指朝着一个目标所进行的动作,同时也是一个结果,表示了一种“转换的结束”(endofatransformation)。因此,成为国王的第三步就随着祷文“etperpraesentemtraditionemnostram,omniumscilicetepiscoporum,caeterorumqueDeiservorum”(您是我们神圣传统的守护者,教会的守护者,上帝神圣的仆人)而结束。 在国王的对面站着神职人员。他们的作用很复杂。神职人员是一个集体,他们拥有神圣的力量,有着将国王转变为拥有神圣力量的存在。尽管这份加冕礼艺术中没有提及,但是国王治愈疾病“国王恶魔”(thekingsevil)的神圣力量是通过主教为国王涂抹圣油获取的。他们提议甚至强制执行一项契约,国王必须发誓保护教会和他的人民并成为一个优秀的基督教国王,才能够举行他的加冕礼。契约同样也是过渡仪式的一种要素,例如订婚与结婚。在另一方面,神职人员也被视为拥有主权的人民代言人,因此由他们授予国王政治权力,这种权力来源于罗马传统中的populus。最后,神职人员是上帝与凡世之间的调解人,授予了国王作为神职人员和人民之间中间人的地位:QuatenusmediatorDeiethomimumtemediatoremclerietplebisconstituat. 在国王和神职人员之后的第三批主角,是法国的贵族。在《兰斯加冕礼仪书》之后,《年加冕礼仪书》是第二个提到贵族参与到国王加冕仪式之中的文献。“贵族”(peers)的概念是一个距离当时较近的概念,大约出现在十二世纪的晚期。他们是当时文学创作中的常客,就像《歌中之歌》(chasonsdegeste)中想象的查理曼时期贵族一样。他们第一次参加国王的加冕仪式可能是在年路易八世的加冕典礼上,也可能只是在年路易九世的加冕典礼上。这些在加冕仪式后支持王权以及伴随着国王登上王位的贵族们在这一仪式上的出现体现了大贵族的参与以及对王权的服从。这一特征在加冕礼之后的和平之吻仪式(riteofthekissofpeace)中得到了体现,和平之吻与敬意和忠诚之吻有关。在场的教职人员和大贵族各六人表现了人数的平衡,然而,教职人员的优势是站在国王的右边,因此他们能够像有更多特权。 次要的人物首先是封建领主和国王的官员。这些重要的世俗人士在加冕典礼,或者说是加入到国王宣誓仪式和戴冠仪式中的骑士仪式(riteofknignting)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王室总管为国王穿上绣有金色百合花的鞋子,勃艮第公爵为国王配上金制的马刺,王室总管(或他的代表)在国王被授予宝剑之后帮助国王携带宝剑,在仪式的剩余时间里,在弥撒期间,直到回归王宫的游行里,他都为国王背负着这把脱离剑鞘的宝剑,这标志着这一过渡仪式的结束。 最后这些参与者有些学者可能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实际上很可能是微不足道的:普通民众。在国王的誓言以及一些祷文中提到了人民的存在,但是都是非常简短的。在仪式开始时,国王第一次宣誓后,两位主教请求他们的同意(posteainquirantaliiduoepiscopiassensumpopuli).在国王第三次许诺后,一位主教(或大主教)问人们是否愿意成为这个王子的臣民(ipseepiscopusaffaturpopulum,sitaliPrincipiacrectorisesubjicere,ipsiusqueRegnumformafidestabilireatqueiussionibusillusobtemperatevelint),此时神职人员和民众一起回应,“愿意!愿意!”(Fiet!Fiet!)国王在宝座前的最后承诺是“在上帝、神职人员和人民面前”做出的。(coramDeo,cleroetpopulo)。最后,在结束仪式的圣歌中,人们一起颂唱Kyrieeleison同时钟声响起。因此,人民的存在大多是被动的,仅仅是群众的象征;可能只有少数世俗贵族和市民被允许进入教堂的中殿,而其余的人挤满了大教堂的入口,就像《兰斯加冕礼仪书》的序言中所描述的那样。 我考虑的第二个问题是:加冕仪式举行的地点是哪里?在这里当然要强调仪式所发生地点兰斯大教堂的重要性。在三份加冕礼仪书——《兰斯加冕书》、《年加冕书》和《最后的直系卡佩加冕书》制作完成的时候,年路易八世、年路易九世和年腓力三世加冕的实际教堂仍未完成,这并不重要。大教堂不仅仅是举行仪式的场所:它在决定仪式各阶段的地形方面起着很大的作用;它在仪式中有着积极的参与地位(尽管在文本中没有提到),教堂经过了精心的布置:墙壁、柱子和地板覆盖着挂毯、帷幔和地毯,就像国王自己将穿着新的长袍一样。教堂空间既不是完全静态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当然,教堂的一些部分肯定是更重要的:颂唱席(choir)以及圣坛(altar),神圣的中心。正是在这里展示王室象征物,正是在这里这些象征物获取了神圣的力量传递给接受他们的国王,正是在这里仪式的主要参与者,宗教力量的主要传递者大主教和高级教士们就座(etdebentessesedesdispositaecircaaltareubihonorificesedeantadoppositumaltaris)。正是在圣坛的前方,国王跪地接受涂油仪式以及获取王室象征物,特别是王冠。在大多数情况下,国王都坐在一个稍高的位置,《兰斯加冕礼仪书》中有所描述:一个略高的平台,有一些台阶,位于正中心,接近颂唱席的边缘,也就是说位于凡世和宗教的分界线之上。(paraturprimosoliuminmodumeschafeudialiquantulumeminens,contiguumexteriuschoroecclesieinterutrumquechoruminquodpergradusascenditur)。年的加冕礼仪书表明,当国王接受了王权象征物并加冕以后,主教将会把国王安置在平台上的宝座上,以让他可以看到所有人(insedeeminenteundeabomnibuspossitvideri)。 在《年加冕礼仪书》中也出现了另一个神圣空间:国王的宫殿。在加冕的当天国王离开他的宫殿并在加冕仪式后回来。当然这座宫殿(palatium)指的是兰斯大主教的宫殿,也就是国王在兰斯的住处。然而他并不是兰斯大主教的宾客。根据中世纪的“招待住宿权”(ledroitedeG?te),这里应当是国王的“家”。仪式开始之时,他就在床上(exeunteautemregedethalamo)。在这里我不同意杰克逊的一点是,他认为在《查理五世加冕礼仪书》之前没有任何出现“床”的迹象,但是“床”的确出现了,这里的thalamus意思就是“床”而不是“卧室”;此外,在《查理五世加冕礼仪书》中确实提到了来接国王的是两个主教,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确实在《年加冕礼仪书》中没有提到是两个主教,但是却提到了当国王离开床的时候,“主教们中的一个”(“oneofthebishops”)颂唱祷文“diciturhaecoratioabunoepiscoporum.”似乎有理由认为在这一时期两个主教来迎接国王的形式就已经出现。 我不知道杰克逊关于“沉睡的国王”(thesleepingKing)形式出现在十四世纪的讨论是否正确。对我来说,重要的是不要用过于死板的逻辑和错误的历史决定论来解释加冕礼,使它成为“加冕礼、受洗仪式和骑士册封仪式这三种仪式的结合”。 人们甚至可以加入第四种仪式在里面:主教的任职仪式。虽然国王的祝圣加冕仪式确实和他们都有关系,但是我认为这些相似之处是因为不同仪式之间有着必然相似之处,如受洗、骑士册封,以及婚礼、授职仪式,当然还有葬礼等。 让我在这里解释一下为什么我更愿意称加冕仪式为“过渡仪式”而不是“就职仪式”:国王的祝圣加冕仪式远不止是就职典礼那么简单,因为它暗示了地位和权力的变化,或者更准确地说,提升。如果我们需要进行比较,实际上也存在很多广义上的过渡仪式。例如,前面提到的国王的“睡眠与觉醒”。睡眠是一种净化仪式,为一段经文做准备;而觉醒是一种分离仪式,是过渡的序曲,正如阿诺德·范特内普所展示的那样。当然,也可以用维克多·特纳所说的“阈限”阶段来描述。至于两位主教则承担了这一分离仪式的助手角色。与葬礼仪式中“假装复活死尸”相比,“唤醒国王”是一种颠倒的葬礼,这里的“唤醒”不是送一具身体去他的安息之处,而是为这具被唤醒的身体带来新的生命。 在一场过渡仪式中,不仅有着固定的地点——在分离仪式前所处的地点,在转换发生时所处的地点,通过过渡仪式接受了新的更高的权力时所处的地点。同时还有这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特定空间的运动:从宫殿到大教堂;从大教堂外走向送回颂唱席和圣坛的大门时的时间点(这是一个出色的“阈值”点,是国王和他的随从从凡世空间踏入到神圣空间之中的节点);以及最后从教堂回到宫殿。有一个词汇在文本与图像中反复出现:processionaliter。这一系列运动联结起来了几个空间形成了一个闭环。这个闭环中的这一切,如果不是宗教性的,就像圣坛一样,也一定是具有魔力的。所有这些元素就构成了作为“过渡仪式”的君主祝圣加冕仪式,而不是一场简单的“就职典礼”。 “什么时间”(when)这个问题很好回答,加冕礼仪书写道,仪式最好在星期天举行,这显然是为了加强仪式的宗教和神圣性质。 “如何”(how)这一问题可以通过分析仪式的结构,从使用的物品和不同的仪式如何连续进行得出答案。虽然没有提及“守夜”之类的习惯,但是兰斯加冕书中已经提到了关于仪式举行前的“准备工作”。为了迎接国王的“转变”,为国王准备了特殊的王座,它“是魔法与宗教力量的标志和贮藏处”。这个座位,作为一种象征物,可以类比古代印度的空王座,或基督教早期和拜占庭艺术中的hetimasia(属于上帝的王座或只放置着一个十字架的空王座)。 第二,大主教们唤醒国王,扶他下床,离开宫殿的行为,表明了国王与世俗的分离,并在向大教堂行进的过程中,向着神圣移动。 教堂内的仪式大致可以分为八个阶段,每个阶段意义不同: 1.进入。国王和两位主教在门槛上停了一下,走进教堂。有一个走向颂唱席的队伍;国王接触到这个为了圣坛保留的神圣空间中最神圣的部分;仪式中重要的次要人物(主教和贵族)都坐好了。 2.圣油瓶。接下来是由圣雷米修道院的修士们手持的圣油瓶(hollyampulla)进入教堂,他们在教堂内继续庄严的前行,圣油装在神圣的瓶中,换句话说这一阶段就是这一仪式中最神圣的物品的到来。这是“圣化”(sacralizing)过程中的顶点;神圣的膏油,它的容器和圣油瓶这一遗物的出现强调了这一圣物与民族之间的联系。(兰斯和年的加冕礼仪书标志了这一圣物与涂油加冕仪式联系进一步密切。) 3.契约。根据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神圣罗马帝国等加冕仪式中的誓言,法兰西的君主做出自己的宣誓。到了这一时刻,仪式的第一阶段已经完成了。这时,圣德尼修道院院长已经把王权象征物放在了圣坛上,在它们接触的瞬间这些象征物就获得了神圣性;国王站在圣坛前脱下了旧的长袍:这一刻标志着分离仪式的结束。 4.骑士仪式。国王的主管为他穿上鞋,接过勃艮第公爵递来的马刺,他从大主教那里,通过一种涉及圣坛和剑鞘的复杂仪式,接受了一把使他成为教会与世俗守护者的武器——宝剑,并委托王室总管将剑从剑鞘中拔出来。 5.涂油仪式。圣膏由大主教在国王的头上(如古代以色列的大祭司和国王,主教),胸部,肩膀之间,肩膀上,手肘上,最后,稍晚一点,在手上涂抹。年的加冕礼仪书已经指出,在尘世中所有的国王中,只有法兰西国王拥有从天上来的油膏的光荣特权。尽管如加冕礼仪书的标题表明这是一份记录国王涂油和加冕的手抄本,但是在这一部分里重点都放在了圣油瓶在教堂中的运送以及涂油礼上。正如大主教所言,国王双手受膏后,就像《旧约》中的国王和先知一样,就像被膏立后的大卫一样(benedictusetconstitutusRexinregnoisto,superpopulumistum)。最后他请求上帝平静地看着这一切(huncgloriosumregemN)。 6.接受王权象征物。王室总管为国王穿上了蓝色的短袍(蓝色后来成为了法兰西国王的象征颜色);在短袍外面为国王穿上一件披风,它翻在左臂上,就像教士的长袍一样。然后,大主教将戒指戴在国王的手指上,这象征着王室与天主教信仰,或许也象征着上帝与他的人民缔结的婚姻。随后,他的右手接受象征王权的权杖,左手接受一根短杖——这份手抄本为这一根短杖提供了最古老的证据——“正义之手”maindejustice(virgaadmensuramuniuscubitivelampliushabentedisupermanumeburneam),当然,它标志着正义也是王权最神圣的职责。最后是两个最主要的王权标志:王冠和王座,王冠是贵族们拥护国王戴在头上的;王座则是国王展现自己完整的高贵与权威的座位。随后,国王宣布最后的誓言,他以一种公开演说的口吻大声念到,“coramDeo,cleroetpopulo”,这句话来自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加冕仪式中的祷文,因此尽管不涉及罗马教会或教皇,法国国王自己承担了“皇帝”的义务。祝圣加冕仪式的最后以主教为国王献上和平之吻和忠诚之吻结束,这时,钟声敲响了,教士们颂唱着圣歌,在场的群众则以Kyrieeleison回应。 7.弥撒。随后的大弥撒似乎是附属于涂油与加冕仪式的,但是它包含了一项重要的事件,表明了国王的新身份以及他作为王室成员过渡到了身兼“世俗”与“宗教”两重身份:国王同时以国王与教士的身份参与了圣餐。 8.最后,“聚合仪式”。国王,如今已经是是完全的国王,离开了这个神圣的地方,他把仪式用的沉重的王冠换了一个轻一点的游行用王冠,返回王宫,但是他显然是带着更大的权威回到王宫里,就像那把出鞘的宝剑一样。加冕礼仪书中没有提及是否要举行盛大的晚宴,但是很有可能。正如范特内普所指出的那样,这是一顿公开的宴席,常常用来结束过渡仪式。 尽管借用了一些中世纪早期盎格鲁-撒克逊人、加洛林、神圣罗马帝国加冕书中的内容,但是直接继承自《兰斯加冕礼仪书》的这本《年加冕礼仪书》标志了“属于法国的一系列加冕礼仪书以及加冕仪式”的出现。对于圣油瓶的强调、百合花的展示以及正义之手的出现——这一系列法国宫廷创新的出现——以及在仪式中出现的圣德尼修道士、圣雷米修道士、兰斯大主教和贵族们都标志了在仪式本身和仪式语言上,法国君主的意识形态变得更加独立,甚至包含了较之所有其他基督教统治者的优越感。 这些仪式表达了圣路易统治下的法兰西王国在国王和教会之间取得的平衡。通过一步一步审视仪式的过程可以看到它如何被精心准备,通过参与者所占据的位置、仪式、誓言文本、祈祷和圣歌、游行、从一个空间到另一个空间的移动和动作——这些仪式避免将一种权力置于另一种权力之上;每当其中一方似乎占据主导地位时,就会有人努力重新建立平衡。只有在国王登上王位的那一刻,他的地位才最终超过了高级教士和世俗贵族。大主教在加冕的国王面前摘下他的法冠,恭敬地亲吻他,贵族们也纷纷效仿。当国王离开教堂时,他面前举着一把未插鞘的剑,遮蔽了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的十字架。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sushisr.com/speegk/7269.html
- 上一篇文章: 6部经典的香水电影,你都看过吗
- 下一篇文章: 读书为你,耶路撒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