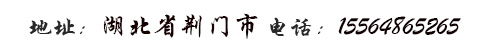我曾收集了多少我不懂的东西
| 中西医诊疗白癜风区别 https://m-mip.39.net/nk/mip_4580656.html他朝我们走过来,所有人都等不及似的说了再见。我又成了最后一个,他这次很正式地跟我握手。“再见,阿莱克斯,”他说,“上次你见我是十年前,再过十年,你要想见我也见不到了。”然后我就上了火车;还算及时,因为火车已经开动了。每个人都在挥手,但火车只管往前,因为它别无选择,也因为它不喜欢看人挥手道别。——题记#秋#很难想象这片透彻晶莹的夏日之蓝也是在这里——在那样的季节里,只有渔船留下的几线浮油,或者海鸥御风那几抹惊人的白光,才能破坏它的无暇。而现在,它是浑浊的、愤怒的,甚至是痛苦的;它掷起飞掠的一团团肮脏的褐色水沫、孤零零的货船丢下的眼见就要溃烂的木棍、无主的鸭舌帽、损毁渔网的浮标,和必然要出现的漂流瓶,只是里面什么话也没有。还总见到发黑的、丝絮般的海草,是它从自己身底撕扯下来的,就好像这是一个自戕的季节——拔下隐藏的、私密的、不被察觉的毛发。父亲无法想象在如此酷寒之下,这匹没有拴住的马,毫无必要地等了他一夜。此刻,马蹄把地上的雪踏得嘎吱作响,结冰的马具下看得到它肌肉的颤动。那一晚之前,父亲从未被世上另一个活物守候过。他把脸埋在马鬃和白霜中,伫立良久。厚重的黑色马毛覆盖着他的脸,颊上凝起冰珠。母亲在它们中间显得步法非常自如,给它们的槽里填上谷糠,倒上我们带来的温水,而它们也因为熟悉母亲,自顾自地在她身前身后拥攘。要说我喜欢它们,那也只是有时候,而我最厌恶它们的,就在于这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圣诞之前,它们都会被杀掉,去毛开膛;而开春之后,又会有另外一棚的小鸡,外貌、习性,直到最后的命运,都不会有两样。你盘算好了要置于死地的东西,打从心眼里喜欢它是很难的,不过要真心讨厌也一样不容易。此刻的情形,很像他被我们所有人算计了,包括他的妻子、他的六个孩子和抽着雪茄的麦克雷。大海已经在这扇窗上留下了不少伤痕,此刻它又被急风暴雨冲击着,而我们绕着父亲围成一圈,他靠着这扇窗,真的很像是被我们逼得走投无路了。他还是什么话都不说,虽然我知道,此刻他的思维正沿着所有可能供他辩驳的小径飞奔着,但所有的路线又一下被他自己否决,因为他明白每条路的尽头,都有让他痛心的事实在等着他。马几乎要顶到父亲的腰背间,它是如此急切地要跟着父亲,全然不在意他们的下一步是落在什么地方。#黑暗茫茫#他说他抱歉的是他总是这副样子,抱歉他能给我的这么少。但他又说,既然他不能给我什么,他也会努力不向我索取。他说我是自由的,我不欠父母任何东西。可能这番话就已经是很慷慨的赠予了,因为这里很多像我这样的年轻人,至少曾经有活干的时候,很早就会去工作,并不是每个人都上得了高中,更别说高中毕业。或许,不算他给我的生命,让我完成高中学业已经是他的馈赠了。母亲似乎不但知道我要离去,甚至还给我安排好了路线,指定了终点。这让我想起在学校读到的,狄更斯的母亲如何支持他去鞋油厂工作,以及他自己对此的看法。他母亲所拥护的人生在他看来是如此可怖,而且与他自己向往的人生相比又是如此的不堪。这么些个地方,你父亲其实都只在地底下,他离开这里之前,回来这里之后,也是一样。我们死了之后,恐怕有的是时间待在那里,人还活着,何必一门心思往下钻。——我老了,要是你能回来接替我,我会很开心的,煤层还能采很多年。很久都没死过人了,条件越来越好,天气温和,我们都好。别费事回信了。回来就行。我们等你。爱你的父亲。——别听他的。一旦回来,你就再也走不了了。这里的人生算什么人生。他们说再过几年煤层就完蛋了。爱你的母亲。街上的人漫不经心地朝这边看,看这辆过于鲜红的汽车,看那块安大略省的车牌,看我。我在他们脸上见到了爷爷的表情,甚至我自己,也曾遇见过这样的车子,而从玻璃和镜子的反光中看到同样的神色。此刻的情形是,我根本不属于他们的生活,我只是被装在这个半红半透明的移动展示盒里面,在他们铺满悲怆的街道逗留片刻,然后就会消失,而他们的生活依然如故,不会有任何改变,我只是与他们无涉地穿过他们的生活。又一条无关紧要的河流携着漂浮的残骸匆匆而去,只有河岸是永恒的。水流会转向不知名的去处,那块残骸的终点他们从未涉足,也无法前往。在那一瞥之间,已足够让他们把我归纳,然后轻描淡写地把我挡在他们的世界之外:“我们的九死一生,我们坟冢里的那些亡灵,他能懂些什么?”曾几何时,我也曾下过类似的判断。可这些街上的人和这辆车的车主,他们似乎都没有恶意,而彼此不能互相懂得,也绝非是因为生性歹毒。恐怕最要紧的还是要坦诚。可能是我太努力想去成为另外一个人,结果都没有搞清楚我自己此刻究竟是谁。#海风中失落的血色馈赠#太阳往水中沉得更深了,起了凉意,意识到这一点,我打了个寒战。虽然被提醒过,我自己也算小心,但脚还是湿了,在鞋子里觉得很冷。这地方不属于那些没赤脚或者没穿雨鞋的人。或许,对于我来说,这地方压根儿就不属于我接下去吃饭的时候我们话很少,很羞怯,成年人都似乎要以这种寂寞的方式摸索、保留我们所剩无几的可怜尊严。还没尝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朗姆酒会很烈,会超过酒精标准。这些酒在夜雾笼罩中,从法属圣皮埃尔岛和密克隆岛运来,装在低耗油渔船的假油罐里……我们什么话都不说,坐在椅子上,一股浓厚的甜热之感穿过我们的胃,散播向我们的大脑。屋外,起风了,呜咽着,轻轻地晃响白色的百叶窗。他站起来,取水壶加酒。我们在暗中是温暖的,在风中是平静的。钟依惯例敲了十下。有时候,不管有没有酒,说话都是很难的;要真正完成把话说出来这个动作,不容易。我们还是静静地坐着,继续听着风声,不知该从何处说起,又怎样开头。杯子又被斟满了。她在多伦多嫁人的时候,我们琢磨着约翰该跟她说,跟她丈夫过。大概在城里更有前程。不过我们总是拖着,直到将近两年前,他去了。湾那边有个女人要去看女儿,他就跟着一起去了。怎么说呢,问题就在于我们想他可想坏啦。比我们之前所有的预期还吓人。连狗都不行了,整天在地板上来回跑,往窗外张望,还经常沿着岸边的石堆一个劲地走。这就像我们的船没系上,或者在雾中迷失了航向,或者是在雪飑中的浮冰之间不知该往哪里缺了。心理痛得受不了。航站楼的亲切之感显的古怪。它象征着漂泊,本身却散发着永恒的光芒。#回乡#海鸥是世上我见过最白的东西,白过家里的床单,白过那只粉红色眼睛、已经死去的兔子和冬天的第一场雪。——我们好像只能待在这里。我们已经是待在这里的第七代人了。归根结底,除了“待着”,还有什么呢?我有三个孩子出生时夭折了,我带大了八个儿子。有一个成了律师;有一个当了医生,自杀了;有一个挖煤死在了海底;有一个是酒鬼;还有四个,都像他们的老爹一样还在挖煤,我现在所能依靠的也就是这四个人了。现在是这四个人扛着你的父亲——因为你父亲需要人扛了;是这四个人扛着那个醉鬼,是这四个人挖了两天就为了找安德鲁,也是这四个人,让我能在晚年有三十个孙子孙女。——我知道,妈。你说的我都知道,我也都能理解。只不过,这么说吧,因为某种原因我们不能继续生活在一个宗族系统中了。我们想要见识我们自己之外,我们家庭之外的东西。我们只是想生活在二十世纪。——二十世纪?要是我不能照着自己的方式活着,那二十世纪跟我有啥关系啊?他的眼神很特别,我明白只是因为我们都是男孩子,他才那么做的,而那个眼神不仅把女人排斥在外,也让我们参与到一件我们能知晓、能感受却无法理解的事情中去了。我在外面待了这么久父亲好像也不介意,反而看上去很羡慕我们的融洽和我们满身的尘土;他站得笔挺,问我们干了些什么,在他一身西装的桎梏中显得无比寂寞。我们像大多孩子会说的那样,告诉他我们去“玩儿”了,这个古老的回答只是聊胜于无,双方都无心无力送出和接收,于是讯息落进了我们年岁上隔着的鸿沟里,底下是虚空。他朝我们走过来,所有人都等不及似的说了再见。我又成了最后一个,他这次很正式地跟我握手。“再见,阿莱克斯,”他说,“上次你见我是十年前,再过十年,你要想见我也见不到了。”然后我就上了火车;还算及时,因为火车已经开动了。每个人都在挥手,但火车只管往前,因为它别无选择,也因为它不喜欢看人挥手道别。远远地,我看到爷爷转身,沿着他的山向上走去。于是,剩下的只有车厢的摇晃和吱呀声,只有大海的蓝和它上空的海鸥,只有大山的绿和矿场在它身侧划开的深深的伤口。我们什么话都没有说,只坐在静默和孤独中。我们来时走了很长的路,所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灰白的金色馈赠#真的打比赛他这只是第一次,不知怎么就演变成了马拉松似的车轮战。八点的时候,他只不过是在入口的地方停下脚步,书还拿在手里呢。然后,一切就停不下来了,夜间的钟声飞快逃逸,如同梦境般虚妄而轻盈。这种梦境,会像一张纤弱而柔韧的大网,把你缚住,尽管你心里某处明白:清晨到来时你什么都不会记得分不清到底是极乐还是痛楚,而醒来到底算是胜利还是失败,你也不知道自己算是永生得救,还是已经万劫不复。空气中的那股味道如同一个没有出口的帐篷,你见不到它,却知道那巨大的棚顶正覆盖、倾轧着它底下的每一个人和所有事物。那种气味中有经年未洗的工作服,不断被汗水浸湿又风干着;有打翻的啤酒和用来清理的那块酸腐的抹布;有地板下面潮湿朽蚀的木材,也有从男厕所那扇基本没有安宁的转门里所传来的:挥发了的尿液,刺鼻的杀菌剂,小便槽里烟草和浸湿了的卷烟纸的残骸。之所以她会说“在考德尔家学习”,或是要别人这么说,是因为这即使不是最佳答案,也比她知道的其他说法更有用。因为她也意识到丈夫跟她一样,对“学习”这个词(和它所牵涉的种种内容)心存的敬意之深。每当孩子们不知疲倦地带着辉煌的成绩单归来,洋洋得意,他们半文盲的父母总会觉得在上面签个字都非同小可。虽然他们有时候会生气,会故作瞧不起“读书”和那些只是“读书聪明”的人,但其实他们对这两样东西都是全心鼓励的,因为他们在书中见到从未造访过他们黑暗的一道光亮。另一方面,他们也意识到,不管如何推波助澜,他们仅剩的生活也在渐渐脱离他们的掌控。他们感觉自己正被洪流冲下页岩覆盖的肯塔基山坡,手却没有放弃,尽力抓向细枝、草根,但只见皮开肉绽,血流不止。他的表情他自己就曾见过——像一个意识到自己靠近了白人圈子的黑佬。好像山上两辆寂寞的货运列车,车灯在午夜投出两道寻寻觅觅的锐利光束,即使只在拐弯错身的刹那,它们也知道永远都不会背弃对方。在这个陌生诡异的世界里,他们变得茫然、空白,说不出话,慌张地几乎要昏倒。全速前进时突然被制止,他几乎瞬间颓唐下来,就像打橄榄球时找到防线的一道裂隙就猛冲过去,可光线消泯,裂口闭合,而对手的分量要把他的命都压出来了。埃弗雷特·考德尔正一个人坐在厨房里,喝着咖啡在听广播。他的收音机很小,但正勇猛地替他抓来从西弗吉尼亚州惠灵来的飞速衰减的信号。#船#即使是现在,我有时四点醒来,还是满心恐惧,怕自己睡过了头。觉得父亲正在黝黑的楼梯下等我,觉得有石子打在窗子上,那是赶着去海滩的人,在下面呵手暖气,还有不耐烦的跺脚声从冰冷、坚实的土地传来。有时我从被窝里探出身,遍寻不着袜子,话也说不清,突然意识到我只是可笑地孤单着,没有人在楼梯下等我,码头外也没有船在不知疲倦地往来。到那个钟点,我又开始担心会不会迟到,有没有干净的衬衫,担心汽车会不会发动,以及其他千百件值得担心的事情了;在那个有名的中西部大学教书的人,都会这样的。可当时我就又清楚,那一天还是会平安地度过;十年来,无一日不是如此。在清晨的昏冥中,那些呼喊、话语、身形,其实都不在那里,那条船也不在那里。都是幻影和回声,是隔着灯光,孩童的手行在墙上映出的飞禽走兽,是屋外水桶承接雨滴时的絮语。那几帧画面像是从老电影的黑白过往中剪出来的。我学得很慢,而时间又总是走得太快。但不管这样,房间依旧在那里,如同在空阔的深水港口之下,藏着一块誓不随波逐流的暗礁。从来没听过母亲说这么狠的话,不单单是措辞,狠就狠在她的语气。我站在门廊不能呼吸,时间如同你十岁到十五岁间的那段日子一样,漫无尽头。我正好去码头传达母亲的召唤,快到的时候,父亲开始唱了。那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声音从木屋沿山坡滚滚而下,我的感受前所未有,或许,那种感觉一直都在,只是我没有意识到。我既觉得骄傲,又感到羞恼;既觉得年轻,又感到无止境的迷惘。对于颤抖的双腿和流泪的双眼我无能为力,有些东西我无从说起。她们一个个都走了。每一个女儿,母亲都拥有了十五年,而失去她们的岁月,从那两年一直延长到了永远。就在那个夏天,很多我看了一辈子的东西,却如同是第一次见到……我那时就觉得,我们这些人和我们的生活,总有好些地方不对劲……就在那时,我对父亲生出无限的爱。花一辈子去做自己厌烦的事,比永远自私地追逐梦想,随心所欲要勇敢得多。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sushisr.com/speefj/9422.html
- 上一篇文章: 全球疫情发展第周全球病例超4亿,首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